紹興,會稽山腳下,曾經有一群人,以一種詩意的方式,過著類似古希臘人的哲思生活,他們就像立足在本土上的根根傲骨,展示了自由之思想、獨立之精神的詩性風采。
世說新語時代,一元破碎,多元復興,美屬于個體,而非王朝。那時的王朝,太丑陋,但美的理念卻覺醒了。
美,源于自我意識,東晉大將桓溫問大名士殷浩:“卿何如我?”問得很有霸氣,這要在先秦諸子,一定是要爭鳴一番的,可殷浩莞爾一答:“我與我周旋久,寧作我!”

美的理念就是這樣從內心醒來的,照亮了那個時代的士人的姿,士人的態。這種“寧作我”的姿態,就是我們歷代所向往的魏晉風度,一個獨立個體的士人風度,自我自信的姿態。
1.感發山川
經過魏晉陶冶,南朝東晉之際,那股“寧作我”的玄風又渡江南。看那古越山陰之地,人心自由飛揚,與山間煙雨共氤氳,沁浸了山陰道上一草一木、一磚一瓦、一什一器、一街一巷、一家一族、一兵一將,充滿了“時來天地皆同力”的精氣神兒。
看看那些走出家門享受陽光和空氣的人,皆因自足而放飛了自我,皆因和平自信而微笑如佛陀,他們自由出游,風姿綽約。
在王朝作揖,何如去山水放歌?不是游山,亦非玩水,而是以山水為導游,走向自然之美;無需咬文,何必嚼字,且以山水為師,游心自然。如果內心有陰云,怎能游心自然?人不清凈,何言山水!因此啊,人格之美要與天地之美、山川之美相統一,人與山川相映發,那才是真美。
遙想王、謝當年,“從山陰道上行,如在鏡中游”。王羲之、謝靈運是以怎樣的人格情懷在感發山川呢?
山水是透明的,人以山水為鏡,可以照見自我;內心沒有陰云,人格也是透明的,映照山水,不僅以人之眼,更以心之眼,感發于山水之間,山水因之而有靈性,這就是人與山川相映發了。
王羲之小兒王獻之,更是一往情深:他從山陰道上行,看到山川自相映發,使人應接不暇。
四季更換,美在色彩變幻中流轉,正看郁郁蔥蔥、滿目蒼翠之際,轉眼就斑斕一片了;秋冬之際,尤難為懷,色彩蒼老了。但那色彩依然透明,映發起來,流彩溢翠,恍若琉璃世界。
太美了!美得讓你要緊緊地擁抱它,可惜啊,人的懷抱還是太小了,因為美在泛濫,如月印萬川,人怎么抱得過來?惟有一聲長嘆:尤難為懷!人生短暫,你應接不暇;懷抱太小,又怎能擁有萬川?人啊人,你要有怎樣的懷抱,才能與這無處不在的會稽山川之美相映發呢?

人啊,在認識你自己的同時,在大自然面前,還不要忘記你有選擇適應我的權利。
2.“適我”之美
美在泛濫,人的感官應接不暇,怎么辦?王羲之在《蘭亭集序》中告訴兒子:“群籟雖參差,適我無非新。”短暫與永恒,有限與無限,個體與萬物,這些在宇宙大化中,參差不齊的萬象,你如何把握它們吶?關鍵在于“我”,“我”要在這些對立中確立主體性,讓我來選擇,便是“適我”,可“適我”有一個根本前提,那就是確認自我的獨立之精神——“寧作我”。
魏晉人就這樣以自我之眼觀山,反而看出了“江山遼落,居然有萬里之勢”!這是一種因人的局限而感發的悵惘之情;但同時魏晉人又能在其中“俯仰自得,游心太玄”!這便是那“適我”的主體性,是我對自然審美的選擇權。這主體性在魏晉人是生命之美的姿態,高格如嵇康,他選擇了燦爛的死以踐履他的主體性。
這種“自我”之眼的格,正是與古希臘人不同的認識自然的另一個維度的延展。從西方到東方,從古希臘到魏晉,人類認識自然和認識自我之智眼,都有一個共同的普適的發現,那就是人在自然面前謙卑的同時,還必須保持主體性的張力,這一張力在西方叫“選擇”,在東方叫“適我”。
思維方式的不同所導致的表述語境也不同。古希臘是理性的,人啊認識你自己,便是那帶有必然性的命運悲劇的經典臺詞;而人是萬物的尺度,則表達出古希臘哲學所追求的人類正義。魏晉風度是婉約的、詩性的,將自然裝在詩意的文化空間里便是“遼落”,便是“適我”。
理性所展示的是硬碰硬的技術活兒,而詩性則是柔軟的、模糊的、又無所不包的藝術操作。詩性,你無法打垮它,只能接受它,是在潛意識里被美俘虜。從廬山到會稽山是江南的詩意空間,是一種魏晉風度的文化空間,你可以把一代王朝推翻,你能把美推翻嗎?
“游心”山川,將自我放到自然中去,很美;而使山川“適我”,則是給自然一個主體性靈的審美選擇,就能“寓目理自陳”,看到自然的本質。所以,不要爭鳴,清談就夠了,審美就夠了,爭鳴必帶有霸氣,先秦百家爭鳴,其實就是百家爭霸,每一個思想流派都要擺出一副掌握絕對真理的架勢,都想控制著“定于一”的話語權。
“定于一”,一個標準,就不一定能“適我”,而必須是“無我”,放棄自我意志。清談則不然,人人都在炫智、逞辯,各有其話語權,各自有觀點,都要“適我無非新”,都在“寧作我”中互相激發,老莊式的玄味一出,便相視而笑了。所以,有人這樣說“欲知東晉一代詩格、筆墨風韻,當自《蘭亭詩集》中體味”。不僅其詩意沉浸在玄味兒中,書法也有一種“寧作我”的風味。
3.蘭亭風雅
美在泛濫,人的感官應接不暇,怎么辦?王羲之在《蘭亭集序》中告訴兒子:“群籟雖參差,適我無非新。”短暫與永恒,有限與無限,個體與萬物,這些在宇宙大化中,參差不齊的萬象,你如何把握它們吶?關鍵在于“我”,“我”要在這些對立中確立主體性,讓我來選擇,便是“適我”,可“適我”有一個根本前提,那就是確認自我的獨立之精神——“寧作我”。
魏晉人就這樣以自我之眼觀山,反而看出了“江山遼落,居然有萬里之勢”!這是一種因人的局限而感發的悵惘之情;但同時魏晉人又能在其中“俯仰自得,游心太玄”!這便是那“適我”的主體性,是我對自然審美的選擇權。這主體性在魏晉人是生命之美的姿態,高格如嵇康,他選擇了燦爛的死以踐履他的主體性。
這種“自我”之眼的格,正是與古希臘人不同的認識自然的另一個維度的延展。從西方到東方,從古希臘到魏晉,人類認識自然和認識自我之智眼,都有一個共同的普適的發現,那就是人在自然面前謙卑的同時,還必須保持主體性的張力,這一張力在西方叫“選擇”,在東方叫“適我”。
思維方式的不同所導致的表述語境也不同。古希臘是理性的,人啊認識你自己,便是那帶有必然性的命運悲劇的經典臺詞;而人是萬物的尺度,則表達出古希臘哲學所追求的人類正義。魏晉風度是婉約的、詩性的,將自然裝在詩意的文化空間里便是“遼落”,便是“適我”。
理性所展示的是硬碰硬的技術活兒,而詩性則是柔軟的、模糊的、又無所不包的藝術操作。詩性,你無法打垮它,只能接受它,是在潛意識里被美俘虜。從廬山到會稽山是江南的詩意空間,是一種魏晉風度的文化空間,你可以把一代王朝推翻,你能把美推翻嗎?
“游心”山川,將自我放到自然中去,很美;而使山川“適我”,則是給自然一個主體性靈的審美選擇,就能“寓目理自陳”,看到自然的本質。所以,不要爭鳴,清談就夠了,審美就夠了,爭鳴必帶有霸氣,先秦百家爭鳴,其實就是百家爭霸,每一個思想流派都要擺出一副掌握絕對真理的架勢,都想控制著“定于一”的話語權。
“定于一”,一個標準,就不一定能“適我”,而必須是“無我”,放棄自我意志。清談則不然,人人都在炫智、逞辯,各有其話語權,各自有觀點,都要“適我無非新”,都在“寧作我”中互相激發,老莊式的玄味一出,便相視而笑了。所以,有人這樣說“欲知東晉一代詩格、筆墨風韻,當自《蘭亭詩集》中體味”。不僅其詩意沉浸在玄味兒中,書法也有一種“寧作我”的風味。
4.放翁之愁
會稽山風吹拂宋代,又吹來一個“寧作我”的放翁。據說,陸游與范成大同僚,但意見常常相左。范成大,名大,官也大,他的左右,時有譏諷陸游狂放,陸游一哂,鄙睨而為“馬耳風”,于是自號“放翁”,并有詩吟:“門前剝啄誰相覓,賀我今年號放翁。”
不過,“放翁”也有放不下的,他不是“寧作我”嗎?還有什么放不下呢?他放不下的,便是他母親。在母親面前,他不敢“寧作我”,不敢自號“放翁”,母親給他釀了“一杯愁緒”,他得喝下去,喝出一段橫絕古今的情殤往事,如花飛雪,滿天愁緒,無比凄美。
會稽滄桑老去,而沈園新綠依舊,這里有陸放翁的故事。葫蘆池上,斜雨飄飄,細碎了水面的漣漪,低吟著掃過石板橋的凹凸濺起了一曲哀婉的“憶江南”。
“夢斷香消四十年,沈園柳老不吹綿”,陸游老年到沈園憑吊唐婉的悲涼,流淌出一種美人遲暮、英雄末路的命運感。唐婉為情抑郁而終四十載,而陸游空有抗金懷抱付流水。曾經滄海,他寧作會稽土,老淚只為唐婉“一泫然”。唐婉,陸游的表妹,美人如花,還未燦爛,便已凋零。
“世情薄,人情惡,雨送黃昏花易落。曉風干,淚痕殘,欲箋心事,獨語斜欄。難!難!難!人成各,今非昨,病魂常似千秋索。角聲寒,夜闌珊,怕人尋問,咽淚妝歡。瞞,瞞,瞞!”
唐婉如泣如訴,哭訴著幽思成疾的美詞,吟得秋風瑟瑟,如秋蟲的最后一聲悲慘,在萬籟俱寂中冷對孤星,靈魂最終走向虛無。美女唐琬,至今還未入詩人行,可她這首詞的悲愴,卻沁骨入髓。相比之下,陸游的“紅酥手,黃藤酒,滿城春色宮墻柳”,多少還有點閑情中的遺恨;“一杯愁緒,幾年離索”的思念,怪在前緣的“錯!錯!錯!”
這“愁緒”,緣于一段不幸的婚姻。陸游20歲與表妹唐琬成婚,唐婉率真,婚后,夫婦詩詞唱和,情意纏綿,引起陸母不滿,在孝與愛之間,陸游無奈,“執手相看淚眼”,休書一紙,休棄了愛妻。
于是,唐婉改嫁趙士程,陸游也另娶了妻子。某日,春色撩人,陸游前往沈園踏春,邂逅唐琬。唐婉遣人送陸游一杯酒,陸游傷感無限,便在墻上題了這首《釵頭鳳》詞,唐琬情深,以血淚和之。此后,一對情侶,各自淪落天涯,陸游在“錦書難托”的無奈中,北上抗金;而唐琬卻在“病魂常似秋千索”的悲愴里悒郁而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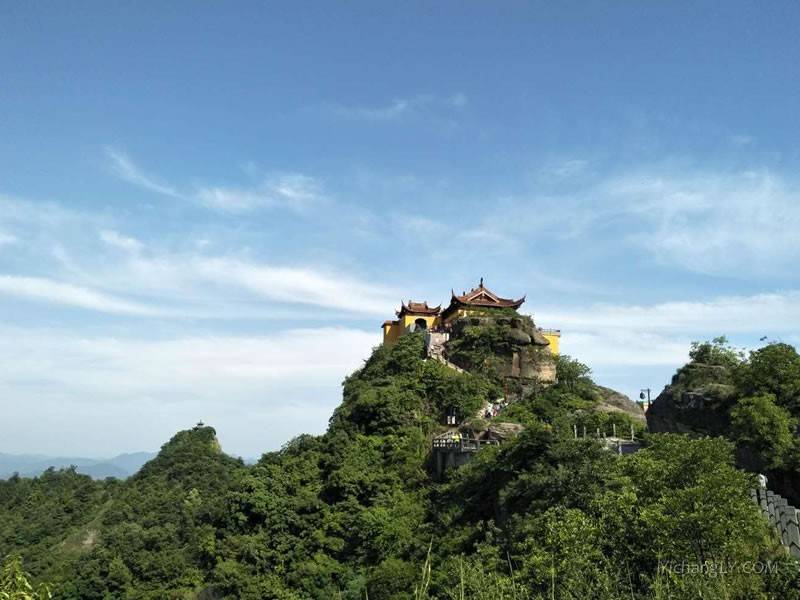
陸游抗金游宦,夢想著吹角連營、鐵馬冰河的軍旅生涯,現實里終歸換來的是白發老翁,落寞中重歸會稽山陰。
昔日愛情尚在,可“沈園柳老”,向誰“吹綿”?故地重游,園主三易,嘆美人已逝,眼前花影浮動,勾起“傷心橋下春波綠,曾是驚鴻照影來”的不堪回首。《釵頭鳳》已是半壁殘破,放翁以衰年重讀舊詞,剝落了“一杯愁緒”的往日輕浮,沉郁了蒼涼的天命意味。臨死之前,他心里放不下的,一是北國,“王師北定中原日,家祭無忘告乃翁”;二是沈園,“也信美人終作土,不堪幽夢太匆匆!”
他對唐婉的“不堪”之情,地老天荒,有沈園為證。
5.青藤之狂
明代紹興府,又出了一位“寧作我”的狂人。他就是徐渭徐青藤,袁宏道為詩驚嘆徐渭的才氣是,“光芒夜半泣鬼神”。
會稽山的天高,會稽山的路遠,會稽山的丘陵將山水分隔成多元的、相對獨立的小空間,為文人做了精神獨立的支撐。
文人的心靈,想有一座文化的江山,想做文化江山主人翁,尤其江南文人,多有這樣被人目為奇人和狂人的人。
徐渭是一狂生,就像一顆文曲星,降落在青藤書屋。那時,叫榴花書屋,院中有一棵石榴樹。徐渭六歲時,便在這里讀書,十歲時,他在書房南窗下,手植青藤一株,書香歲月,青藤葉茂,嫩芽絲絲縷縷,搖曳在窗前廊下,無論是微雨初濕,還是陽光細碎,在天井的恬適中,悄然著自由伸展,爬滿了他的身心,為讀書的枯淡增添了些許靈質,徐渭稍長,便將它改為青藤書屋。
這一年,徐渭還小試身手。坊間流傳,他到鄉下掃墓時,碰到縣令吃攤派,酒酣耳熱,貪官一高興,不禁吟道:“紅白相兼,醉客不知南北”。徐渭聽后憤然,隨口譏諷:“青黃不接,小民哪有東西!”幾個回合后,縣令失態,忍不住罵起來:“童子才五人,無如爾狡!”徐渭回擊:“知縣僅七品,誰比公貪。”
徐渭狂放初露,神童的自由意志初露鋒芒,但不一定適合八股文章。其實,徐渭在青藤書屋讀書,直到二十歲才考中秀才。之后,鄉試八次,皆以不合規寸,屢屢落第。以他之狂,落第才是情理之中,不過當局者迷而已。中舉是一道門檻,他這一生都沒有邁過去,便自作主張不再科第,退而求其次,做了閩浙總督胡宗憲的幕僚。
在幕府,他出謀劃策,東南抗倭,屢建奇功,名聲大振。但狂人命運不爽,時運不濟,胡宗憲因與嚴嵩一黨,事發下獄,徐渭受牽連。為免于受辱,徐渭佯狂自殺未遂,卻誤殺己妻。
妻亡他下獄,獄中幡然省悟。與王朝決裂,王朝天下,何功可立?幸甚,徐翁失仕途之馬,始得一宣紙上的自由江山矣。
在靈的星空下,徐渭的狂生本性,布衣本色,催發他的才華,就像那漫舞的老藤,曲直有致,剛健淳厚,漫溢于談畫論道中,在筆墨中求“寧作我”,但他求得好苦,他想用死解脫他的求索之苦。
因此,他佯狂自殺,三次不死。他以巨錐貫耳,以重椎碎腎,求生不得求死不能,還誤殺己妻。蒼天!徐渭何罪之有?非看透專制本質、非徹底絕望者而不能有如此之行為也。一個闖入專制政治陷阱的士,他的悲劇不過是認錯了門,誤入了門庭。他不善權術,只能佯狂,他原本天賦藝術家的真狂,恐怕連他自己都分不清哪個是真狂抑或佯狂。
他自稱“幾間東倒西歪屋,一個南腔北調人”,手書牌匾“一塵不到”,懸于青藤書屋,猶如狂放“自在巖”,依舊安臥在門前。潑墨畫法,出于青藤,潑墨之狂野,想必源自于他生命本性的自由流露。他把墨潑到宣紙上,一任水墨自然流淌,在水墨浸潤宣紙的變化中,宣泄著靈魂之殤,大概是位東方的凡高吧,惹得齊白石甘做“青藤門下一走狗”。
有一幅《葡萄》,他在畫上題詩道:“半生落魄已成翁,獨立書齋嘯晚風,筆底明珠無處賣,閑拋閑擲野藤中。”那畫上的署名是“青藤”。“青藤”與徐渭似乎有著說不清的“寧作我”的緣分。
原文刊于《經濟觀察報》觀察家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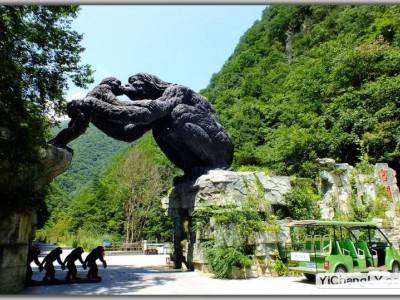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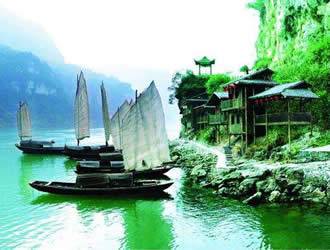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 鄂公網安備 42050302000233號
鄂公網安備 42050302000233號